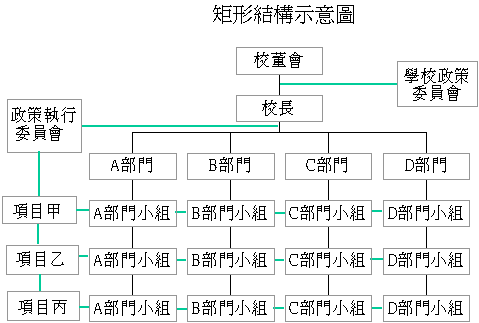認 識 學 校
─── 一種組織形式,其結構及改革的建議
第一章:引論
教育行為的存在,可謂與人類的歷史同樣悠久。遠古時期,人類在日常生活中以單對單的形式,隨意無計劃地將自己的經驗及對自然的認識以口傳身教的活動方法,傳授他人。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形式已不能適應需求,教育逐步從社會生產和生活中分離出來,並逐步形成群體的教育模式。據記載,中國古代已針對不同教育對象分“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滕文公上」);且依據行政地區的級別分別管理“…家有塾,黨有庠,朮有序,國有學”,更進一步計劃了分級教學內容“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令而不返,謂之大成”;並將辦學目的定為“建國君民”“化民成俗” (「禮記.學記」)。這種群體教育模式,其實已具備了現代社會學家所認定的組織模式之一般要點:也就是一群人就共同的目標,以適當的方式聚集,並根據確定的工作程序進行運作。
西方教育的發展亦類似中國。在西歐、古希臘以及羅馬奴隸製時代,有為奴隸主貴族培養子弟的學校,教授體操、文法等。中世紀時期,有教會、行會學校,以及大學等,為地主階級培養子弟。但這一類的學校,學生人數少,教育過程亦是採用個別施教的形式。實際上,無論是中國或其他國家,古代教育管理模式,從形式、內容上皆有很大的局限性。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暴發的工業革命,誘導社會對勞動力量、人才的需要,大規模生產形式延伸到教育教學領域,學校在人員數量、設施建置、教育內容等方面,都進行了徹底的改變。學校做為社會成員的存在,不得不融入社會發展在個體、群體間所產生的協調、依存、進步之關係鏈結中。人類在他們發展經驗中,深深地理解溝通與合作,不僅提高生存能力,且會令他們取得個人力量所不能取得巨大成就“human beings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their activities and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y can achieve more through collective effort than individually.”。而組織的出現,便在實際上提供滿足人類這種需求的形式。隨著社會發展,人類生存的環境也越來越複雜,要達成目的所需處理的信息量越來越大,所需操縱的程序越來越多,個人能力越來越無法勝任。於是,組織形式便應運成為社會成員存在的必然模式“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the most pervasive and dominant social institu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is is especially so in industrializing, industrial, or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The 20th century has seen an explosion of specialized organizations to meet the need for the mass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re are organization that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meet a vast array of our daily needs.”[RI Westwood (1992)]。當代教育學家亦開始借助社會學的組織概念,分析並探索學校的存在與發展。
事實上,學校教育要在社會上發揮其最大的效能,其本身內部對教育目的、教育內容、教育秩序、教學時間、教學方法、學生編班等,都應有妥善的安排“使他們在各方面能象一座用巨大技巧做成的、用最精緻的工具巧妙雕鏤著的鐘一樣”做到有條不紊的運行。(「大教學論」,捷克.夸美紐斯)這也就是現代的學校以組織模式存在於社會的最大理由。因此,對學校的認識與研究便不得不從組織的認識開始。
第二章:學校組織及結構
組織理論發展至今已近百年歷史,關於組織的定義莫衷一是。但任何一種牽涉社會的組織定義,無不從“人群、活動、合作、目標”等基本元素出發,進而強調組織是以某種結合方式形成整體獨特的面貌存在於社會當中,正是如此,組織效能才會得以真正的發揮。我們僅以Shein的組織定義來認識周圍學校。Shein認為“Organization is defined as rational co-ordination the activities of a number of people for the achievement of a common explicit purpose or goal, through division of labour or function and through an hierarchy of authority or responsibility.”(Shein,1990.見課程講義。)這個定義,強調了組織內部的分工合作必須建立在理性化的權責體系上。人性的弱點再一次提醒組織的擁有者和管理者,在一群人當中,是難以用自由運作的方式去達成既定目標。每個人都具有不同的思維和行事方式,而做為組織,就在於能夠協調和利用這種差異。從字面上講,上述的定義包含以下的內容:
1.A number of people they have a common explicit purpose or goal.
2.Division of labour or function
3.an Hierarchy of authority or responsibility.
4.Rational co-ordination the activities.
依據上述定義,學校作為一群人(學生、教師、其他工作人員)的集合體,是以組織形式的存在,她必須會有一個整體的共同目標,並依據目標的要求建立某種形式之組織結構:確定組織成員的職位、定明權力與責任;合理分工;協調活動,規範運作方式。就這個定義,我們來認識“學校”。
-
學校目標(Purpose or goal):
事實上,所有組織,都是為了某個特定目標而存在的。組織內的每一個成員都圍繞這個目標並盡力為這個目標工作。明確清楚的目標,是組織存在的關鍵因素。清楚的目標能讓員工明白工作方向和要求,令他們更容易掌握取得工作成效的方法,有利於提高組織的效能。對於香港的學校,教育署已事先頒發學校教育目標及目的之指引文件,要求各學校參照執行,更推出“目標管理”的具體方式。各辦學個人或團體在籌建過程中,也會根據自身的特點,擬定學校目標,以“傳遞社會文化”為己任。學校將要求每一位成員(入職者)認同這些目標並必須以此做為工作的方向。雖然這點略帶有強制意味,但它無疑是學校生存的不二原則。學校的創建者及指導者或說是行政管理人員,將協調每位入職者(員工)的個人目標與團體目標,以產生組織效能(Effectiveness)。
-
分工及專業化(Division of labour or function)
作為組織目標的達成,其過程並非單一化的簡易操作,特別是發展迅速的現代社會,組織目標及其任務的達成,遠非個人的力量可以包辦。昔日聖人孔夫子獨力培養“弟子三千”的偉績,已不在可能。這其實也是前文所講的組織在當代社會之能夠且必然存在的原因。這些複雜的操作過程必須由組織成員分別承擔進行;而分工的合理化程度,將直接影響工作效率(Efficiency)的產生與提高。香港學校的組織成員分工,教育署已頒發行政指引,原則上依據職員的能力及專業特長,將其納入已劃分的事務和科務兩大功能類群下。事務類別中,又依據工作性質的不同,劃分生活服務、財務出納、校舍管理等。科務類別也依據年級、學科,分派教師承擔教學工作。這種工作的安排,有利於員工熟悉其本職工作,促使其專業能力的提高,從而提升成員的工作效率。[Hoy,Waynek.&Miskel,Cecil G.Miskl(1996)]
- 組織結構(Hierarchy of authority or responsibility)
所謂的結構是“組織內各構成部分或各部分間所確立的關係”之形式。[F.E.and J.E.Rosenzweig(1979)]而這種形式將確立成員間的溝通方式、工作規範;也因此確立管理人員的權力來源及責任範疇。它促使組織在形式上成為一個整體。在組織中,結構形式影響甚或決定了組織的性質與效能。因而,規劃和建立適合組織目標的組織結構是組織過程的重要環節。對此,古典組織理論的創始人之一Max Weber提出理想的組織結構應具備有以下六個特徵:
-
分工和專業化(division of labour):將常規性的工作以固定的方式分配員工,而因此促成員工工作技巧、熟練程度的提高,達成專業能力的形成。便以產生良好的效率。
-
職業評級與獎懲(promotion based on ability and achievement):員工按能力、資歷確定升遷。也依據此標準確定人員的僱用、獎懲。
-
等級體系(hierarchy of authority):級別分明、上下有別。上級管理下級,下級向上級負責的垂直成員關係。
- 規章制度(rules and regulations):清楚明瞭的工作規則,讓員工按章辦事,並以此為準則協調彼此間的關係。
- 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離(separation of officials from ownership):組織的投資人與組織的行政管理人員分開,讓管理者能理性地發揮其工作。
- 純粹人事關係(impersonal orientation):組織成員間,除了工作目的以外,不存在任何的個人關係,公事公辦,不感情用事,保證行政管理人員能理性工作,發揮效率。
具備上述六個特徵的結構,令組織運作依定規章,行動條理分明,可預測性強,便以管理。同時,權力來源有據可依,避免人為的隨意因素的干擾,因此使組織更加理性更具效能。這個正統(ideal type)的結構模式,直至今日,依然得見其全部或大概於社會的各類型組織中。香港的學校亦是其中一個例子,其基本具備了上述的特徵。
雖然各個學校的具體架構有所不同,特別是在水平分劃上。但就垂直關係而言,都依照政府規定的層級設立,即學校由校董會負
責,校董會確定的校監負責聘請校長。各學校依據需要設立
一至數名副校長,確定主任職位,聘用教師職員,招收學生。
整個學校自上而下,層級設置,形成職位不同、權責不同、
上下從屬的等級體系(hierarchy of authority)。如右圖所示。
這一系列官階職位,在教育規例、津助守則以及學校制定的
章程中,基本上都有列明權責,強調上下級間指揮與服從的
關係,同時說明任職人員的專業資格,包括聘用、解僱、薪
酬、升遷等,規範分工專業化(division of labour)與職業評級(promotion base)。教育署同時發出教育條例、教育規例、資助則例等行政指引,列明學校的教學工作、學生入學、升級留級、離校等,各校也參照指引制定相應規章制度(rules and regulations),做為員工的工作準則。這一切,顯然可以說明香港學校具有明確的組織結構,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依據Max Weber的理想組織結構模式原則形成的。
- 協調運作(Rational co-ordination the activities ):
一個群體有了具體目標、分工、結構體系之後,尚必須將成員的每一項分工活動整合成為有序的、朝向既定目標發展的行為,才是真正完整組織的過程。每一個職位的管理者執行其結構定義賦予的權責,依據既定的
規章制度(Rational principle理性化原則),通過“計劃planning、組織organizing、引導leading、控制controlling”[Stephen P, Robbins Mary Coulter,(1999)]的方式,對屬下的活動activities協調規範在組織目標(goal)的實現軌道上來。這便是理性協調的作用。目前香港的學校之行政管理人員,也同樣根據相應的權責進行協調管理教師的工作。為此,教育統籌科及教育署於1991年9月頒布推行的“學校管理新措施”,要求參加的學校釐定清楚教學目標、預備程序綱要、校務計劃書、校務報告、建立教師工作評估、設立檔案紀錄及問責制度等,目的也在於強調學校必須以規劃、引導等方式,協調控制學校成員的有序活動。這其實也包含了組織形式的一個特徵“planing of scheduled activities”(參見課程講義Session1.02)的體現。
根據上述四個方面的考量,學校作為組織存在的形式已是不容置疑,雖然各所學校的架構並不完全相同,但其組織結構的原則依然從根本上借重Max Weber的理想模式、也就是被人們稱之為科層制度(bureaucracy)的理論組成。[參見課程講義Session2.02及Hoy,Waynek.&Miskel,Cecil G.Miskl(1996)]
第三章:科層體制的缺陷與學校改革的建議。
科層體系制度,從形式上規範組織行為,令組織內部成員的行動循規蹈矩, 管理者的權責分明,確實能有效地擺脫人為的因素,是所謂“最有效率、最理性化”組織模式。難怪Max Weber可以斷言,科層體制是社會發展的結果,是複雜的大型組織必須奉行的原則。
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民生活質素不斷提高,對於自身發展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對組織的要求也不在只限於提供抵抗外界生存危險的保障格局。組織成員已要求組織提供發展個性、實現自我、展示個人認知的空間(參見課程講義Session1.06: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於是,科層體制的許多弱點便暴露出來。特別是它嚴格的等級設定、繁雜的條規章則更是否認了個人價值,壓抑了個性及員工潛能的發揮。“阻礙組織內部成員的彼此溝通,扭曲創新改革的意願”。員工因循守舊,缺乏工作活力,久而久之便成為僵化呆板的“組織人”(參見課程講義Session2.07)。“官僚主義”“教條主義”也因之成為這類組織行為的貶義標籤。而這種情況在學校組織中亦頗常見到。事實上,學校組織成員分工,並不僅是要依照等級制度的方式進行,它同時應參考教師的學習專業進行安排。專業等級又以不同的標準考量,如非教育專業的博士、碩士,在具體教學上的作用並不被認為比合格教師強,薪酬更非比普遍教師高。這種情形,遠不是科層體制可以解決的問題。況且,科層組織強調結構穩定性,而這種假設,顯然帶有封閉系統的意味。但在目前科技發展日異月新,組織內外環境瞬息萬變,資訊交流無孔不入,要生存並適應環境,組織已不可能置身於變革潮流之外。特別是學校作為社會系統,其特有的開放性(參見課程講義Session3.0),令這種假設更不可能。學校以“傳遞文化、培養人才”由目標,而與社會環境相脫節的學校是不可能培養出與社會相適應的人才。如此看來,純粹用科層制度的組織結構方式來駕馭和管理學校組織,無疑會限制了學校目標的實現,從而陷入打擊教職人員的工作積極性、降低工作效率、影響學校組織整體性的有機效能及工作計劃執行的惡性循環中。
依據系統理論的公理表明,每一個系統都存在最佳的結構形式。學校作為開放性的社會系統,同樣可以通過對內部結構的調整,對組織系統內部各式各樣的活動狀態,進行最佳秩序的組合,以求形成系統的“整體最優化”[蕭南槐,1986]而這個最優化的過程,將是學校組織的運作結果,得以有效地達成目標的必要手段。針對科層體制存在的弱點,我們可以嘗試從以下相關的兩方面尋求最優化的結果:
- 結構改革
科層體制其中一條阻礙組織活力的規定是“等級體系”,它是以信息指令垂直傳遞的方式為特色,但也因而造成組織內溝通的自上而下單向性,令組織運作中的失誤難以向組織決策層反饋;同時,部門之間的協調操作因“上傳下達”的過程而延誤工作時機。再者,現代社會的環境越來越複雜,組織內部的專業劃分越來越細,同時,每一項工作計劃所牽涉的部門、人員也越來越多,“現代組織极其精確地依賴於水平的關係,因為有如此之多的專業化的觀點和如此之多的聯繫,而任何一個管理人員都不能單獨使這些交往得以順利進行” [F.E.and J.E.Rosenzweig: N.Y.McGraw-Hill (1979)]。因此,尋求一種令溝通信息更加方便的模式,即是當務之急的重點。除了日益完善的IT科技控制外,矩陣形式的組織結構,顯然是一個較佳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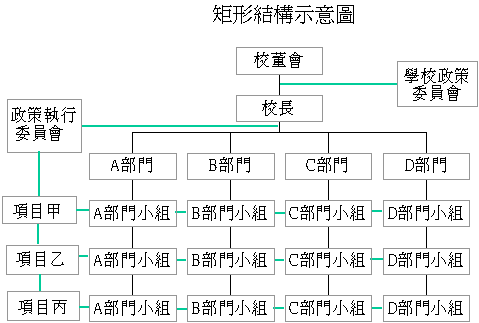
矩陣形式的組織結構,其特有的雙重指揮鏈(dual chain of command)功能,增加了水平方向的溝通聯繫,避免功能部門或專業部門劃分的單一性,其組織內部的指令、信息將同時存在垂直與水平方向的傳遞形式,減少信息流通的時間。而其結構的建立,亦可以根據系統環境的變化與需求作出相應的調整。這無疑使組織的有機綜合能力更為加強,應變能力得到提高。見上圖示意。
- 活動協調
科層體制組織活動的協調,是以等級結構和規章制度加以保障而起作用的。這種方式在學校系統中,因學科部門的水平性專業劃分,在溝通的語言上產生困難,給組織的整體目標達成製造分裂性隱患。因此建議採取以下幾個方法克服這類不足:
-
成立教師委員會,以自我教育、自我激勵的形式讓教職工更加清楚和理解組織的目標,令跨部門、跨專業的溝通更具效益。同時這個委員會,將在形式上制衡校長的集權制產生的獨裁,令教師有更多的機會參與管理與決策。再者,委員會的形式,亦有利克服第一條建議中矩形結構的不足,加強雙重指揮鏈一致性的理解溝通,消除不必要的沖突。其實,成立教師委員會的建議,在1991年教統科和教育署推出的「學校管理新措施 」之改革建議第十項已明確闡釋。問題是時至今日,這項建議依舊有它實際與深遠的意義:許多學校還有待於建設或者發揮委員會的真正作用。
-
成立學生自治委員會,以自我教育、自我激勵的形式讓學生同樣清楚與理解學校教育的目標。讓學生明白社會,包括家長、教師寄予他(她)們的希望,讓學生體會肩負的責任並自己設計今後的發展方向。教育的過程決非單向的指令過程,它是教師與學生互動的過程。再加上現代社會的IT發展,“黑箱作業”式的學校教育,定會背離學生的認知環境而導致失敗。有意識地讓學生參與學校的教育管理應該會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最近教統會在「終身學習 自強不息」報告中,就設計改革的方向和建議,提出“學生為本”的原則,我認為這個原則會是包含學生自治自強的教育。否則,“終身學習”基礎便無從形成,學生走入社會後“終身學習”的理想亦將難以實現。
-
全面質量管理[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W.Edawards Deminy.參見Stephen P, Robbins Mary Coulter,(1999)]香港學校的好壞,在社會人士的眼裡,似乎只看到其會考時學生的總體成績。較少人會關注學校內部的各項運作過程的好壞。而事實上,即使是學校內部的成員都極少研究學校運作的每一細節對學校效能的影響,大家的關注焦點都是表現出來的成績。但根據TQM的理論,最終組織效能的表現,歸咎於過程中每一項工作質量的優劣。再者,TQM的推行,可針對科層體制壓抑個性、工作單調的弊端,提供減少垂直分化的途徑,避免不必要的過細分工,增加工作樂趣;同時其分權式決策,令教師更具責任心,更能發揮員工的潛能,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而事實上,教師對學生的學習質量最清楚、最具發言權。TQM的組織運作方式,也有利於發揮矩形結構的最佳功能,兩者具有相輔相成的結合性。也只有如此,建立高效能學校的目標,才能尋求出真正實現的通道。
第四章:總結
教育行為的發展,隨著社會的進步而由單對單的個體行為,逐步變成群體社會化的組織行為。而學校的產生,為這種發展予以更具體的組織表現。它同樣具備了一般組織所應有的特徵:群體、目標、結構、活動。香港的學校更明確地表現出其科層組織體制的特性:分工、層級、理性、規章、資格、管理。但傳統的科層體制的某些原則已顯然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求,並阻礙了組織目標的完整實現,所以我們建議從學校組織結構、協調管理入手,採取矩形結構模式,建立及完善委員會制度,加強水平方向的溝通,有意識地讓教師和學生參與學校管理決策。並逐步引進全面質量管理(TQM)的方法,改善組織內部活動每一細節的工作質量與工作效率,尋求出實現高效能學校目標的有效通道。
參考書目:
-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Hoy,Wayne K. & Miskel,Cecil G.Miskl(1996)
-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Edited by RI Westood (1992), Hongkong Longman Group(Fast East)Ltd.
-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 a systems and contingency approach: F.E.and
J.E.Rosenzweig: N.Y.McGraw-Hill (1979),3rd edition中譯本:組織與管理
- MANAGEMENT, Sixth Edition: Stephen P, Robbins Mary Coulter,(1999)
A Simon &Schutter Company
- 大系統論: 蕭南槐,(1986)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學校行政: 吳清山,(1996) 臺北心理出版社
- MARY MUNTER’S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nd skill: Maree Bentley (1991), Simon & Schuster(Asia) Pte Ltd.